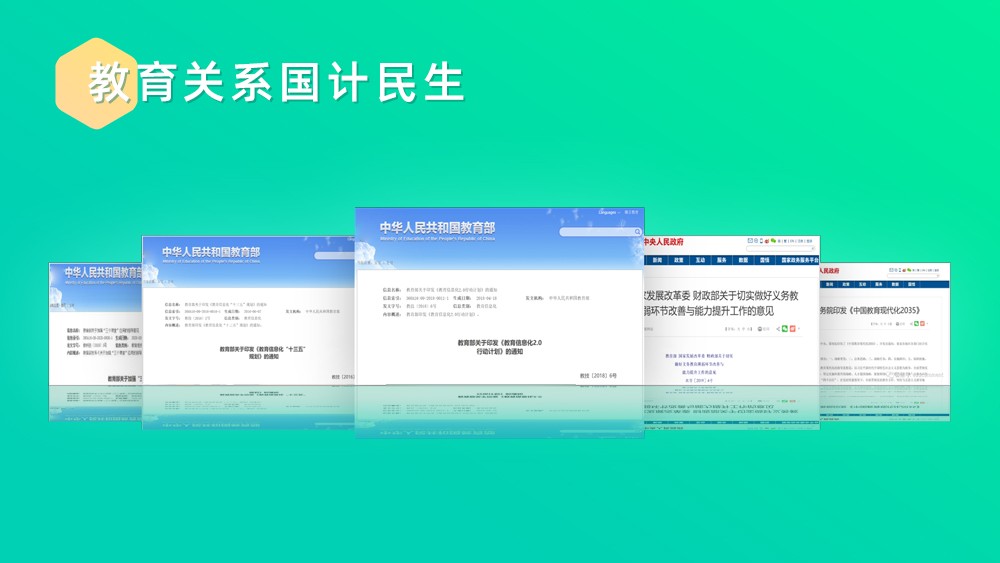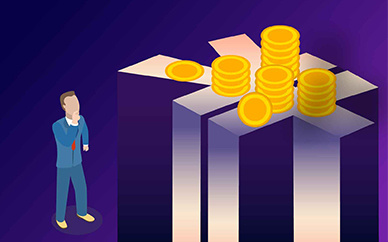“他的身后,代表了我们全部。”
 【资料图】
【资料图】
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volutionäre Anthropologie)的创立者与领导者。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苏恩·伯格斯特龙(Sune Bergström),但他并未得到这个著名父亲太多的荫蔽,他看上去只是一个高挑,消瘦的传统科学家,在2022年10月3日之前,他与所有拥有“学术声誉”的其他科学家一样,做了一些工作,在科学史上留下了名声,最后他会安然离世,把名字留在教科书上,从此走完完满的一生。
只不过,他今日获得殊荣,他的成果不再被视为只属于专业学者与学生们议论的话题。他成为了今日的科学之星,为这个蔚蓝星球上的所有人展示生物学迷人的光彩。
我感到荣幸,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所在领域的第一块诺贝尔奖。长久以来,古生物学被视为电视节目中的惊奇马戏,那些打扮得如同牛仔的古生物学家似乎只需要对儿童负责,为他们提供种用于过渡到青春期的怪兽传说。这种看法将延续到未来,不过在今夜,我们可以乘着诺奖的光荣,展示它本来的严肃姿态。
献上所有生物学学子都耳熟能详的名言作为序幕:
"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若无进化之光,生物学的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一、班驴
这是我讲过许多遍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班驴(Equus quagga),一种漂亮的,曾经生活在南部非洲的动物。它们脾气暴躁,富有警惕心,因此被土著居民霍屯督人驯化为守卫马群的看守,以防夜间马匹丢失或者遭遇进攻。这种美丽的生物在欧洲移民的大肆捕杀后迅速消亡,鉴于它们暴烈而倔强的性格,班驴无法适应动物园的人工养殖,于是,在1883年,随着最后一头雌性班驴的死亡,这个曾经驰骋在非洲草原上的动物彻底灭绝。不过,它们并未在沉默中消失殆尽,在种群数量迅速减少的时刻,有相当数量的班驴被制作成为标本,摆放在欧洲各国的博物馆中。这些华丽的皮毛成为了它们曾经存在于世上的唯一凭证,人们远远地观望它们,追忆昔日南非旷野的风景。
1977年,生物学界著名的天才弗雷德里克·桑格尔(Frederick Sanger)发明了第一代DNA测序技术——“双脱氧法”。这一技术使得快速且低成本的遗传编码读取成为了可能,并为桑格尔赢得了他第二枚诺贝尔奖——不过比诺奖更加重要的是,他的测序技术彻底改变了生物学发展的方向。这几乎是现代生物学的最重要的基石——一时间,大量的测序工作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如火如荼地展开,几乎所有的生物学家都在尝试应用这一技术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在这股“DNA热潮”之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兰·查尔斯·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与 Russell Higuchi 将目光从微生物与细胞转向了德国美因兹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具标本——一头死于1883年的班驴。
这是第一次从灭绝生物身上获得DNA样品的案例。Higuchi 从 0.7g 的组织上获得了两个线粒体DNA(mtDNA)片段,并利用它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灭绝生物的系统发育树。这两百多个碱基对向我们展示了班驴这一神奇物种在整个马属中的位置。就这样,这个短短的小文章奠定,甚至规范了一个未来的学科的大致方向——古遗传学(palaeogenetics),正式诞生了。
由古DNA建立的马属系统发育树
二、木乃伊
我相信阿兰·威尔逊的结果传来之时,帕博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之前心心念念的问题得以解答,而另一方面,他那“史无前例”的工作成为了第二名,他本来有机会成为第一个报道古DNA保存的人,不过很可惜,他被抢了先。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他的自传《尼安德特人》中读到详细的过程。不过我在这里也会简单聊一聊这个有趣的“科学竞赛”。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学术新星的帕博结识了罗斯季斯拉夫·霍尔特尔(Rostislav Holthoer)。作为一个自幼痴迷古埃及的年轻学生,帕博很快与这名来自芬兰的古埃及专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影响下,帕博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古埃及知识的状态,一度开始学习法老的语言——科普特语,甚至产生了脱离生物学进军考古学的冲动。面对两种不同领域知识的诱惑,帕特逐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所有人都只盯着现代的材料,不去尝试研究一下古代的DNA呢?如果能够成功地获得古人的DNA,那么常规考古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将取得巨大的进步:语言的交织,民族的演替,王国的发展……古物与记载只能描述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在那尚无人涉足的领域,似乎还埋藏着更加深刻的真相。
几乎是偷偷摸摸地,帕博开始了他的实验——毕竟这无关于他实验室老板的任务,与腺病毒编码蛋白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他还是开始了模拟实验,将一块牛肝加热至木乃伊化,然后检测DNA的保存情况。熟牛肝的气味显然影响了同事们的心情,不过帕博还是成功地在木乃伊化的牛肝上找到了DNA。然而之后霍尔特尔为他提供的木乃伊样品并未显示出任何DNA活性——于是帕博又只能回到免疫学的研究上,乘着老师没有因为他三心二意而大发雷霆。
几乎是巧合——霍尔特尔为他联系上了德国的博德博物馆,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木乃伊收藏地。经过一系列波折,帕博最终踏上了开往德国的火车,并在这里采集了三十多份木乃伊样品。当他带着样品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实验室时,切片染色的结果却让他倍感失望——几乎无法看到任何细胞结构。然而就像所有科学传奇那样,在黑暗降临时,科学家仍旧没有放弃。帕博在耐性耗完的前一刻,终于获得了木乃伊样品的DNA染色痕迹——毋庸置疑,他找到了古NDA。
他紧接着开始尝试提取古DNA。凝胶的结果非常漂亮,木乃伊保留了大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帕博开始畅想有一天说不定有可能能获得这些古代人与动物的基因,他满心欢喜地写下文章,只可惜,这篇发在德语期刊《古代》(Das Altertum)上的论文石沉大海,似乎没有人关注木乃伊,更不要说,一篇德语期刊的木乃伊文章。
我不知道帕博是否失望,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这项工作——当然他正儿八经的活计还是腺病毒和讨厌的免疫屏障。他意识到,仅仅获得DNA还不能说明更多的信息,因为这些片段很有可能来自于细菌,动物甚至外界环境。他必须完成测序工作,才能说明这是人类的DNA。而正在这一时刻,阿兰·威尔逊的工作递交到了他的手上。无论如何当时的感受如何,这都给与了他长期的信心。彼时的阿兰威尔逊早已蜚声海内外,他是人类演化的专家,是分子钟(molecular clock)的验证者,是“线粒体夏娃”假说的创造者——而帕博呢,他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研究生,偷偷摸摸地实现他对古埃及的狂热爱好。而此刻,学术地位悬殊的两人正在做同一件事,这是一种肯定——他站在了科学的前沿,而他面前,是本来不可触及的历史。
1985年,Nature发表封面文章,Molecular cloning of Ancient Egyptian mummy DNA,作者,唯一作者,斯万特·帕博。文章发表后,他也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兰·威尔逊的信件,搞不清来头的大科学家不了解研究生帕博的身份,便在开头毕恭毕敬地写上“帕博教授”。
帕博的文章,这也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起始点
“或许能让威尔逊给我洗一年凝胶板!”无论如何,属于帕博和古遗传学的时代,开始了。
三、尼安德特人
如果有什么技术改变了生物学,那么我会选择,PCR。
PCR,全称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从1985年这项技术创立开始,生命科学的研究就走向了快车道。在热泉细菌的演化馈赠之下,只需要短短数个小时,科学家就能获得数以千万计的遗传物质拷贝,用以测序,拼接,剪切……可以说,PCR使得生物学正式进入了分子时代,几乎所有的现代生物学研究都离不开PCR对于遗传物质近乎魔法般的扩增——大到癌症研究,小到核酸检测,生命科学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PCR。
当然,拿着零星碎片的古遗传学更是离不开PCR——有什么能比化石碎片里面的DNA更破碎的样本呢?答案是,下一块化石。
就像所有青年学者一样,拿着奖学金,毕业了的青年帕博开始了漫长的的学术生涯。在经历了瑞典,美国,英国,瑞士等等国家之后,昔日年轻的帕博也变成了中年帕博,他留居在了梦开始的地方——德意志。1990年,帕博加入慕尼黑大学,这时的德国刚完成了统一,科学事业方兴未艾。在这里,帕博开始了自己事业的高光时刻。他开始建构完整的古DNA提取流程,时至今日,他的标准也在世界各地的古DNA研究室得以运用。1997年,帕博加入了马普科学会,并扛起人类演化的大旗,就任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同年,他发表了重量级文章:Neandertal DNA Sequences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尼安德特人DNA序列片段与现代人类的起源)。
这就是提取出全基因组的骨骼标本
这是第一篇有关于古人类DNA研究的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帕博借助PCR的强大能力,建构了一套用于鉴别污染,重建序列,恢复系统发育关系的技术流程。或许这听起来并没有那么“令人惊奇”,不过你可以想象,在十多万年的漫长岁月中,DNA分子会在微生物降解,物理化学破坏,以及其他生物干扰的情况下变得支离破碎。就好比碎了一地的乐高积木,而科学家必须在缺乏拼图手册的情况下找到一大堆积木中仅有的那些正确的积木,再拼出正确的形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论文给出了在mtDNA的视角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亲缘关系。这个本被视为欧洲人祖先的"高贵先民”最终被排斥出了现代人的mtDNA谱系,他们未能为现代人贡献mtDNA,早在60万年前便与现代人支系分道扬镳。这一结果极大地打击了欧洲部分民族主义者的自信心,曾几何时,尼安德特人被视为欧洲人的直系祖先,他们将其视为与”非洲猴子”截然不同的生物。然而这种政治上的偏见最终无法获得科学的支持,尼安德特人走下了神坛,而人类的演化脉络,也逐渐开始清晰起来。
2006年,帕博开始着手重建尼安德特人整个基因组的计划。这是首次对灭绝生物全基因组的恢复,而这也是除人类外,第一种人属生物的全基因组测序计划。2009年,帕博公布了第一批测序结果,超过30亿碱基对的庞大信息勾勒出了尼安德特人的方方面面。2014年,完整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得到阐释,现代人,尼安德特人,还有帕博在2010年在丹尼索瓦洞发现的丹尼索瓦人(这也是第一种完全依靠古DNA发现的灭绝物种)——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复杂人类演化脉络开始逐渐浮现。
现代人与灭绝的古人类发生了基因交流,这些古老的婚姻奠定了现代人的模样。非洲以外的人类身上保留有1.5-2.1%的尼安德特基因,而丹尼索瓦人则对亚洲与北美原住民贡献了0.2%的基因占比。原来独属于现代人类的,简单的“走出非洲“变得复杂而喧嚣,这些古老的兄弟姊妹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他们仍有片段寄寓于我们体内,用来凭吊数万年,数十万年前发生在亚欧大陆的风云诡谲。
我们是所有人类的子嗣,大地之上,遍布我们祖先的足迹。
更新世晚期人类族群可能的基因交流模式
四、诺贝尔奖
我相信,这会是一次饱受质疑的诺贝尔奖。因为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或许会发现,帕博并未如同之前的获奖者那样,建构一个精妙的,天马行空的技术手段,也没有发现一个似乎能一下子改变世界的重要结果,你甚至很难具体描述他做了什么。他来自于一个边缘的,公众陌生的,甚至科学团体有时会嘲笑的领域。我们这些处于交叉学科夹缝中的人往往也会如此怀疑自己——我们真的是在做科学吗?
毋庸置疑,古生物学,或诸演化生物学是“无用”的。有时我们往往会找借口谈一点有关于油气埋藏,地质构造,生态改善,低碳环保的大话,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就是一个无用的领域。我们不为公众提供任何便利,甚至科学团体也不需要我们给与什么——这不是DNA测序技术,不是PCR,我们未曾发明什么,我们只是最后的使用者。
但是我们却要回答最伟大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
帕博的得意门生,Magic Fu,也就是我们古脊椎所的付巧妹老师,她建构起了东亚人群与早期欧洲人群的演化历史,在她那里,中国史前人群南北格局、迁徙扩散及遗传混合历史的面纱缓缓揭开,稻作文明的产生不再模糊而迷离,中国乃至整个欧亚的“历史”,正在她手中缓缓成型。而她的同门们,也在世界各地描绘着人类历史的痕迹。而除了人类之外,那些灭绝生物也在研究者的手中逐渐厘清了演化的脉络,灭绝生物的生理特征与形态性状恢复也伴随着古遗传学的深入研究逐新变为可能——那些本来在地下,死气沉沉的骸骨重新长出了血肉,我们真实地恢复了历史,洞察了我们的起源。
数千年来,民族,血统,语言,人种,国家,疆土,信仰,观念,这些伴随人类文明创生的词汇深深地将人类分割为了无数的碎片,在大陆上,我们见惯了战争与征服,在大海上,商船与战舰破开波浪,有时连缀,有时冲突。我们望着彼此,却难以识别彼此的样貌,但在古DNA交给我们的家谱中,我们确乎然能够看到,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一处。
这是巴别塔倒塌后,人类彼此最接近的时刻。
而这所有成就的背后,我们总是能看到斯万特·帕博的身影。(李鑫)
阿兰·查尔斯·威尔逊(1934-1991),他入围了诺贝尔奖提名,但因白血病过早离世